|
好看手机云在线看最火影视 https://www.shoujiyun.net 网络语言泛滥,“废话文学”盛行,加深了人对词汇的“过敏反应”。 一句话讲明主旨、提炼中心思想,汉语文学教育、商业市场强调的功能性,塑造也框住了写作者。 有人谋求流量,有人渴望功名,“每一个曾经有志于写点什么的人,在自媒体时代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感慨”。 以上种种,青年作家李盆总结为:世界上的“熵”在急剧增长,有史以来最大的“现象”浪潮正在远远地过来。而今如何拥有一套好语言,进行一种自由的写作,抑或从事一份愉悦的文字工作?唯有守卫母语,和头上那一小块寂静。 本文摘自李盆《羊呆住了》,原标题为《业余作者如何摸索出路》。因篇幅所限,有删减。 01 对词语过敏的自我诊断 我很好奇,在所有应用中文的群体中,每24个小时会打出多少个汉字,这是一件很难统计的事情。如果不去计较竹纸绢帛和像素的区别,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年代出现过如此巨量的文字痕迹,人们从来没有这么密集而自然地书写过,而且是全民书写。即时通讯和自媒体实际上让汉语的生命力出现了空前的大爆炸。这不是语言集权化和精英化的年代,但从语言生命力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从没有过的黄金年代。 全民书写主要是汉字输入法的贡献。输入法书写是心理活动、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的中间形态,说和写进一步模糊,书面和口语之间不再分明。这种简便和快捷带来的渗透程度,让输入法在文字应用上的贡献几乎可以超过活字印刷。 但输入法中的语义联想和热词推荐,代表了这类工具的一个主要毛病,即高频词越来越高频。活跃汉字越来越集中。一味讨好用户是互联网产品的原罪,输入法也不可能躲掉这个原罪。 2021年上半年网络热词之一:“柠檬精” 每个词汇在过度使用之后都不可避免要面临的命运:所指增生。 这种所指增生,让每个词都像是蝜蝂,在身上背负了太多的额外意指,一旦背上就不太可能卸得下来。 以至于几乎有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把全社会总的人文形态看成一件毛衣,然后把随意一个词语看成一个线头,揪住这个线头,便可以把整件毛衣拆干净。意指背后还有意指,意指是无限衍生的相似性,意指会吞食整个世界。 每个人都会对少量的词汇存在过敏反应。有一些过敏,就来自上述那些高度符号化和所指增生的肥胖词汇。 如果对两个曾经的网络热词进行尸检就会发现,“浮云”“洪荒之力”的猝死,都是所指增生的结果。 几年之前,“浮云”这个词在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它背后最强烈的意指是“网感”“新”“时髦”,使用这个词的人完全不是出于语义需要,而是贪图这种额外的意指,这也许并不是虚荣心那么简单。而当在几个月之后,“浮云”的使用频次过高而失去了新鲜感,人们就开始在修辞的鄙视链上迅速分化,像一队行进的蚂蚁忽然溃散。当又过了几个月的时候,“浮云”已经在互联网上大规模消退,最终在各大企业年会、春晚上稍微回光返照一下,便逐渐落灰了。直到几年之后,仍然普遍存在回避“浮云”这个词的情况。 相比“浮云”,在被一轮一轮的人造热词训练过之后,“洪荒之力”的生命周期更短,面对的阈值更高。如今使用“浮云”的频次已经降低到很低的程度,而“洪荒之力”则面临消失。 这种词语所指的增生,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们对过期热词的过敏,最终是这个词语的死亡,硕大油腻,扔在废纸堆里。 某中文社交媒体的运营团队是最能炮制这种人工热词的团队,每个有动静的热词,都是他们一手发掘并调集流量浇灌,他们在一代人中间用废了不少无辜的汉字。 还有一些过敏,来自莫名其妙的通感,往往找不到原因。 有人从小学开始,就从来不使用“心痛”这个词,而是一直使用同义词“心疼”。只是觉得“心痛”两个字有一种中年人写信的感觉,略微浮夸,还带着弱势和潦倒的味道,甚至能让他联想到他和他爸的隔阂。而这种不能接受一个词的感受,近似于不喜欢一种颜色的感受,可以无限发酵,却像纯净水的味道一样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 还有的人不喜欢“母亲”这个词,因为有一种腰粗和肥胖的感受。也有人不喜欢“却”这种笔画较少的虚词带来的干燥感。甚至还有人会因为形状而不喜欢“万”字。这种过敏一般都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改变一个人的用词习惯,并形成很多很多暗角。人们会在潜意识中直接淘汰所有不喜欢的字和词,通过近义词或者修辞来进行代偿。 这种通感通常来自独家记忆,和私人经验密切相关,每个人各有不同。 审美偏好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敏感,一般称为“特别爱用”。 著名体育评论员杨毅的微信公众号中,平均每周能看到三到四次“漫长”和“漫漫长河”这两个词,这看起来是一种对史诗情绪的偏好,意味着繁忙都市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就如同相声演员“那一夜梦见百万雄师”。 另外,在一些讲话之中,用“当前”开头的段落占到一半以上,对“当前”的应用,类似于一种仪式性的口头手势,一种齐刷刷的排比徐徐展开,说话间仿佛夹带着杀伐决断以及洞若观火两个微微发亮的成语。 还有一些常见的偏好,比如在行文中以形容词作画。把代表局部真理的金句断行加粗,仿佛一切陈述就是为了抵达这一行字。为了一个巧妙的环形逻辑而特意修改主旨。过度迷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语感,写不到一千字就开始喘。或者通过自动书写偶尔发现一个精巧而迷幻的西式文字装置,却不知道如何安放。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修辞传统之下,许多许多的传世作品,实际上都是一种文玩产物,审美也许是好的,却只有一个盆景那么大的格局。人们太喜欢口吐莲花和字字珠玑,最后忘了真正要说什么。 无论是哪种过敏,都是来自文字使用者本身。而词语永远是无辜、透明和中性的。 “废话文学” 对词语的偏见,让这种用于书写的工具反而影响了书写本身,让文字成为文学的最大束缚。在语言文字面前,没有人是自由的,只是这种不自由没有任何不适,代价太低而不被注意。这是一个痔疮一样普遍存在却不显著、也无法根除的问题。 文字本身不应该是阅读的终点,文字本身只是一个起点。文字也不应该是写作的终点,只是设置一个观察和想象的窗口,提示叙述走向或者提示一种意识状态。如果对词语脱敏,减少对修辞的执念,文辞上的钝感往往能成就更多,就像卡夫卡和刘慈欣。 02 不抱目的去写 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文以载道”已经被认为是真理。“文以载道”的训诫把汉语文学牢牢钉死在文学工具化的框架内。 言之有物、提炼中心思想、一句话讲明主旨的语言训练,还有学以致用的教育观念,一代又一代地塑造了所有的人。 “文以载道”的说法来自周敦颐,有必要顺便提一下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从根源上看,儒家思想就是大型组织管理学,让庞大的族群保持现世安稳的同时,也屏蔽掉了更多的可能性。之后儒学又在理论上和其他思想打通,变成了理学。理学在哲学高度给自己找了更多的生存依据,但仍然摆脱不了过于现实的技术性特征,摆脱不了紧缩、反熵、求秩序的组织管理学本质。无论它怎么发展,最终都是画下一条线,而不是擦除一条线。 一盆水泼在地上是不可能留不下痕迹的。儒家思想慢慢变成统治思想,统治思想又被打散成为民俗,溶解在民间。我们以为来到了新的时代,但在主流文化圈,儒家仍然是被抓得最紧的文化稻草。即便是在以西化和潮流著称的文化创意类公司,也不可能摆脱儒家的影响。 在这种土壤中,文化会不可避免地偏技术,文学和艺术都带着难以摆脱的工具属性和有限性。所以必须要反对工具论,文学作品并不应该有什么社会作用,至少不应该特意去考虑这种作用。 在现在的阶段,每种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已经不同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文学的形式本身已经醒来,形式本身具备实在属性,不再只用于表现具体思想或者事物。 除了“文以载道”这一类的目的之外,如今写东西的目的更为现实。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什么事情都是功效至上,什么事情都要有现实回报,什么事情都要量化衡量,什么事情都是要谋求数字增长。我们已经感觉不到写作本来该有的状态是什么。 自媒体时代的作者很容易自我阉割,即便没人胁迫的时候,出于逐利的考虑,也会自己修剪自己。在整体阅读量中占比过半的自媒体内容,都是按照一些原则和目的产出的,而且这些原则和目的,目前普遍被认为是对的: • 讨好读者。 • 引人注意。 • 有传播力。 • 符合流行的观点和主题。 • 反对流行的观点和主题。 • 炫耀技巧和修辞。 • 批量复制爆款作品。 • 应激性创新。 • 凑数量,早点成为一个出过书的人。 • 凑类型,成为全能型作者。 • 想涨粉或者害怕掉粉。 这些目的会损害一个作者身上真正的使命和最初的动机。 每一个曾经有志于写点什么的人,在自媒体时代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感慨,而感慨会变得越来越少。在这个时代,纯粹的写作是一件备受冷落的事情,所有的关注和回报都十分稀薄,更多的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关注,以及同情式的回报。长时间的青灯黄卷之后,作者的写作不可避免地会慢慢变成自己的回声,就像一个人向深潭中投石,对着树洞自言自语。 而写作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自我技术”,它先于所有目的而存在,对一个人的作用不会因为冷清而有任何衰减。 03 业余比专业更有价值 文学史必然是和评价系统结合在一起的,已经座次森严拥挤不堪,而且充满了互惠和互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西方,都已经是齐腰深的名利场。 在这个领域里,充满着根深蒂固的权力逻辑:前人决定后人,已有的决定未来的,有光环的决定没光环的,中心的决定边缘的。 每个时代,只有在当世被人们认为显赫的、影响力大的作品才会找到位置。只有中心的几个名声鼎盛的人物,才会被社会广泛接纳,然后成为大师。个别幸运的边缘人物往往在身后才能进入大众视野,太多太多的书稿从来没有见过天日。 诗人海子 凡是成功的,都会和专业和权威画上等号。很多人崇拜大师、崇拜专业不过是崇拜成功而已。 但其实文学领域没有什么理论是重要的和专业的。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方式,生产任何理论和任何作品,只要能自洽,并且是来自内心的真实声音。 在这个领域内,边缘的、琐碎的、不好归纳的、容易丢失的、没有什么名声的,才是本来面目。功成名就的,高度权威化、中心化的理论、风格、人和作品,并不是全部,文学绝不仅仅是那几个山头。 每个人脑子里都有很多很多没有来由的、琐碎的、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碎片,本来都是富矿,但往往都被忽略掉,只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是“外行”。其实即便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了解了各路大师的经典,也不见得比自己脑子里莫名其妙的念头有价值,这些念头是每个人都有的天赋。 我们总是仰望一些大师如何挥洒天赋,却忘了自己也有,而且人人机会均等。差距仅仅是偏执程度、自觉意识和少许技巧。 对于作者来讲,业余就是最好的方式,业余意味着这件事不是那么重要,不重要的事情才会不扭曲,可以保持敏捷和新鲜。 在身份归属上,作者始终是很难选择的,不管是进入作协,大学,出版机构,还是什么文化圈子,都意味着进入一种权力系统。权力系统中首要的自然会是权力运作,而不是写作本身。对组织行为的关注必定会取代对纯粹热情的关注。 另外一种,如果作者不去投奔任何体制,就在家里全职生产,除非特别有钱,否则必定会被动商业化,很快进入投机状态,定制内容谋求回报。当今所有的出版流程,都是生意为先,所有的自媒体也都是流量至上,没有人可以逃离。 对于没有财力保证的作者来说,想专业化或者职业化,在投靠体制还是投靠市场之间,只能选择一种卖法,或者两边兼顾,变成一个跑场子的人。 在当下,凡是感觉写作没有出路的人,基本都是因为瞄准了两条大路。一条是奔着出书改电影赚钱,另一条是在圈子里出名,被翻译成外语,进入专业机构的视野。这两条路当然都是渺茫的,因为这是别人的路,充满了别人的游戏规则,作者得成为别人才行。 但实际上,写作本来是很简单和很自我的一件小事,只需要一个技能,就是母语。别的都用不着。甚至都不用去宜家费心挑选书桌。 业余就非常好,只有业余才能让这件事真正成为自己的事。保持私人化,保持次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最好的状态。 04 时常搓洗一下文学史 历史就像一辆随意漫游的车,无论怎么走,身处车内的乘客都会默认为是往“前”开。历史还经常会给人一种连续的错觉,好像一切都是沿着时间依次发展的。 划分文学史,最好用的办法是用时间来区分,古典、现代等等,这其实更像是一种记忆法,有助于我们沿着本能把这些东西记住。这种文学史只是一种最能找到共识、最简便易懂的文学史模式。不代表唯一解。 而对于作者来说,这种断代方式毫无意义,一个忠于自己的作者,是不会考虑文学史的走向的,本来文学史也没有什么必然走向。 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并不是什么承上启下的关系,即便后来者受过影响,也不能说是接过前人的稿纸。每个真正独立的作者,心里都有着排他的、互不相干的完整世界观,都会试图用自己的理解方式去统一所有已发生和未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重复的全局性的工作。而且这种认识是不依靠时间而存在的,并没有“历史”属性。但是在后人看来,往往把他们按照页码编进同一本理论书当中,默认他们合力拼成了一个绵延的文学史。 还有很多横空出世的人,很难解释为时间原因,只能说他们是突变型的作者。以萨德为例,萨德横亘在西方知识界,一度让所有领域都无法绕开。而他似乎又与所有时代不相吻合,就像突然出现在装修奢华的大屋子里的一棵酸枣树,无处摆放。萨德不是时间产物,只是恰好出现在了18世纪,他也可能会出现在9世纪或者未来,也许9世纪本来就已经出现过萨德,但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同样的人,相信还有很多很多,但井然有序的线性文学史显然是无法自然容纳这些人的。 萨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 假如按照西方的现代概念来衡量,中国的现代文学似乎出现在更早的时候。至少魏晋时期就是非常早的文化觉醒运动,有着明显的现代性。鲁迅把魏晋时期称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还提到了“人的觉醒”。后来当横贯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越来越纯熟,文学反而开始越来越充满着文玩和学究味道,有的走不出市井,有的走不出山林,有的走不出书斋。 以上所说的断代,是沿着时间来归类整理的方式,下文的流派则是横向分类的方式。这种分类比沿着时间分类更不合理。 在文学史上能留下记录的人,大都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作者变成了百度百科中的人,他们的作品也都穿过变迁剧烈的文化和语境,被洗成了一种面目模糊的语言文物。后来人们看经典,大都是拿着看文物的思维去看的,时间越久、名气越大,附会就越多。尤其是荷马这样的早期作者。 我们对作品和作者的了解其实都十分草率和失真,一个跨时代作家的作品,经过时间与翻译的磨损,除了有个大概轮廓之外,动机、细节和真实的东西就像是锅汽,会随着语境变迁慢慢丢失。 后来的阅读,其实更像是重新创作,所有的作家,都已经被读者重新创作过一万次了。无数人的阅读、评论,让文学史变成了一部误读史。知识界和出版界又把这种误读大量地繁殖、印刷、流传下来,巩固和放大这种误读。 流派,往往就是在这种误读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实有必要按照一种新的分类方式——不是以成果为依据分类——而是以动机分类。 原始驱动力,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坐标。如以下这十几种: 1.无聊。 2.竞争意识。 3.钱。 4.性欲。 5.愤怒或者悲伤。 6.自卑。 7.虚荣。 8.失败感。 9.求真。 10.恶作剧。 11.攀比。 12.讨好。 13.角色扮演。 大部分以作家为第一身份的人,首先也都是“人”,都可以纳入这些原始动机当中来。很多厉害的作家,他们后来侃侃而谈的事情,还有历史对他们的那些认识,都是在有了成就之后顺势而为。很少有人会在早期默默无闻的时候,就意识到后来自己仿佛真的信奉的事情。 电影《公民凯恩》里的线索是玫瑰花蕾,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玫瑰花蕾。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公民凯恩》剧照 太多知名的作家,除了早期作品,后来的工作都是在维护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名声。在早期作品里最容易看到原始本能,就是在那些不太好的,不太完善的片段里。当终于弄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出来,编织这部作品的过程,往往也就是建立防御的过程。伟大往往就是失真。 05 一小块寂静 人是无处可逃的,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 没有另一个地方,也没有另一份更好的工作。没有改天没有来日,没有等一等再说。没有整块的时间,和阳光打在书桌上这种愉悦时刻。 没有灌好墨水的笔。 如果想写,就直接在胃里开始写,在脑子里也可以。在地铁上,会议室里,大中电器门口,交电费的时候,超市二层的膨化食品区,都没有什么妨碍。 除了母语,和自己头上的一小块寂静,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用不着什么群山和地平线,也用不着喝酒抽烟。 在这个社会上,用母语写字,是你唯一能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一小块事情,不大于一也不小于一。这一小块和人没有关系,和神也没有。不用在意夸赞,也不用在意贬低和批评。 不是为了出名赚钱,因为根本赚不了钱。只是自证存在,以及提供一种必要的自由幻觉。 如果你学的是冷门专业,不要担心,因为热门专业也不会更有用。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横穿,横穿系05届毕业生,我的宿舍在五楼。这个专业非常冷门,简直一点用都没有,四十二门专业课都极枯燥,都是绿色封面。所以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从后窗翻出去买韭菜馅饼。 老师也不在意,毕竟横穿马路有什么好讲的。但他还是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启蒙。我的毕业论文是《如何横穿一个郊区》。老师伸出一个手指头说非常好,去研究,知识不一定要有用,不一定要有目的。 我就去研究了。沿着直线从铁西走到水泥厂,途中摔破了皮,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不一定要有用,不一定要有目的。”后来我觉得他说得对,这句话是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 我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负责写所有ppt的最后一页:“THANKS”“Thank you”“thanks a lot”“以上”“感谢聆听”等等,我尊重我的工作,它是我用一只脚来参与社会的方式,也给了我钱,让我用另一只脚来完成自己。还养活了我的猫。 尽管工作和横穿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当时所学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改变了宇宙,毕竟我就是一百多斤宇宙。 感谢这个专业和那位老师。 本文节选自 《羊呆住了》 作者:李盆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后浪 出版年: 2020-11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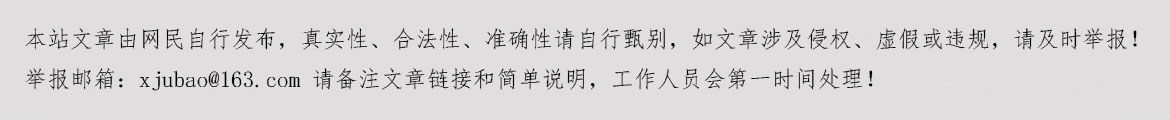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