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花带露,红叶随风。青山界上,天高地阔。立冬时节,我们带着窖藏经年的思绪,重返美蒙。 凝视十五年光阴的距离,我忽然想到一个词——新变。 一 一路阳光,一路微风。我们遇上了青山界初冬时节难得的晴好天气,浅浅的阳光在青山界上暖暖流淌。从锦屏县城驱车两个多小时,九十公里的山重水复,用另一种方式重新丈量了曾经的一段心路历程。 二OO四年仲秋,我受北京一位爱心人士的委托,前往湘黔边界青山界大山里的美蒙村,看望两个受助学生。我早早从锦屏县城乘船溯清水江而上,赶了四十五公里的水路,在清水江和乌下江交汇处的河口下船,然后徒步上瑶光苗寨,沿着深山古道往青山界的余脉攀登,再经过白泥坳寨,到培尾村时已是薄暮时分。当我走到裕和苗寨,浓浓的夜色淹没了我的身影。一位老人指着远处迷蒙稀疏的灯火告诉我:“美蒙就在那里。对面喊得见,见面要半天。”夜宿裕和的那个晚上,美蒙像一道谜,让我猜测了半宿。第二天,我在濛濛秋雨中向美蒙跋涉,先从裕和村往下走,一直走到纵深切割的山谷谷底,再走上古木森森、山路弯弯的青龙岭。那场雨其实不大,但我消耗在路上的时间,足以让雨水浸湿我的行囊和衣服,也浸湿了我的美蒙记忆。 我们这次赶往大山里的美蒙侗寨,驱车翻越青山界,然后从青山界上乘风而来。在我身后,十五年的时空距离和遥想,已经被一双神奇的妙手悄悄折叠起来了。 同行的杨才应老师,也是暌违这个山村十四年了。 还在二OO五年的时候,杨老师在锦屏县特殊教育学校工作,既是学生文化知识的授课者,还是带领学生学习石刻等技能的专业老师,同时兼任义务宿管员和炊事员,他的敬业和爱心,让那些远离家人的孩子对他心生依恋。学校放假了,只有美蒙村一个杨姓的聋哑男孩没有家人来接,这个孩子的父母都在外省务工,家里只有爷爷和奶奶。当时美蒙还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杨老师主动提出送这个孩子回家。那一趟路途,他们下车后,翻山越涧,紧赶慢赶,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哪里黑哪里歇”,在裕和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才走到美蒙。 美蒙,别来可无恙? 一到美蒙才发现,村寨的变化出乎我们的想象。 通村公路有两个出口,一头过干田塝组通往青山界,与通达剑河县南嘉镇、黎平县平寨乡的路网连接,一头下溪边组,出山谷后连接311省道,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村寨里建起了一个文体活动广场,广场的里边,矗立着一栋三间两层木质的村卫生室和一栋三间两层砖混结构的村办公楼,广场外侧的一栋闲置小木楼已经成为驻村工作组的食堂,广场的两端则围着整齐的宣传栏。村里的三处人饮工程,让村民过上了“喝水不用担”的日子。我发现,在沿着村道伸进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太阳能路灯,一盏盏灯笼上都印着篆体的三个字“美蒙村”。 美蒙是锦屏县一个边远的深度贫困村,全村一百零八户四百二十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六十八户二百八十三人,二O一九年初贫困发生率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二四,是锦屏县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村寨之一。村里的劳动力本来就不多,但常年有一百一十余人在外面务工。而今,这个村寨,曾经在贫困的惯性中滑行的日子已经远去,蒙正在发生前无古人的新变。 我们走寨串户,美蒙的变化让我们惊喜,更让我们心情为之一振的是,美蒙村有了扶贫产业,“三变资金”入股飞地公司、东西部扶贫协作富阳对口帮扶“探索三变”投资项目、稻田养鱼、生猪养殖、养牛补助等。其中,“三变资金”入股飞地公司覆盖贫困户五十二户;东西部扶贫协作富阳对口帮扶“探索三变”投资项目覆盖贫困户十六户;稻田养鱼六百三十公斤,生猪养殖四十二头,养牛补助九头,魔芋种植二十一亩。这些数据,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孵化了美蒙人的脱贫梦想。 在溪边组,我们走进村民杨明清的家里,和他们聊家常,他的妻子王秀琴是从贵阳市花溪区金竹镇的一个布依族山寨嫁过来的,说到村寨的变化,王秀琴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交通条件好了。三十多年前,我从花溪金竹镇来这里,在路上就花了四天,好多年了,讲到回娘家我就害怕。现在好了,今年春天我女儿出嫁,我的娘家人只用一天时间就到我这里了。这个变化太大了,像是做梦一样。” 听她这样一讲,我不禁又回想起初到美蒙的经历,联系起今天的所见所闻,真是恍若隔世。 二 美蒙原称“木翁”,意为“被树木遮蔽的村寨”。村子坐落在青山界支脉青龙岭大山上的“观音形”,海拔八百五十米。寨后古木根叶苍秀,老干屈曲,山色苍苍。寨前的山脊上,一排参天古枫顺着山脉的起伏,构成一道擎天的绿色屏障。若是天晴的日子,站在这里向裕和苗寨眺望,对面的木楼、菜地甚至山径上的行人都历历可数,好像一探手,就能触摸到裕和寨边“关口”古树上的枝叶。可是,一条叫做“龙塘”的山溪,从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山界上狠劲向下一劈,美蒙就被隔在了大山上,被大山高高地举着,让绿树浓浓地簇拥着,愈显出静美中的孤独和僻远。在公路修通之前,村民们生产生活中的许多不便由此可想而知。 美蒙是青山界百里苗乡中的少数几个侗寨之一,村民自称“偢家”(生活在湘黔桂交界地区能同时用苗语、侗语和汉语进行交流的族群),生活习俗与当地苗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行“偢家”礼节,唱“偢家”歌,只与“偢家”通婚,哪怕路程再远,是青山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社区和“孤岛”。美蒙居住有张、杨、龙三姓人家。清乾隆年间张姓人从亮江流域的大同村来此地谋生,后回去邀约稳江的杨姓亲戚,稳江杨姓又邀来龙霭的龙姓亲戚。张姓祖先迁来时,此地原居住人群已迁往他乡,田地荒芜。清代至民国,美蒙曾与相距七八里远的培陇、九丢两个苗寨合为一个行政村,一九五七年单独立村。历史上,美蒙因山多田少,生产生活条件差,所生产的粮食难以自给。远去的那些美蒙故事,不堪回首的是人们对自然特别是生存环境的无奈顺服。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的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融进美蒙人骨血里的“偢文化”,不仅仅是符号和仪式,已经成为他们的身份象征和心行的根柢。在美蒙人心中,亮江河畔的故乡才是他们永远的家乡,美蒙只是族群迁徙的临时栖身地,他们总在等待有一天回到故乡去。美蒙的老人去世,得杀猪宰牛给他(她),为让他们能得到,猪牛宰杀后,需用一根绳子一头拴着猪牛脚,另一头则拴连死者的手(男左女右),并交代逝者将所得猪牛往老家方向赶去,认祖归宗。产生这种族群文化心理,是否与美蒙以前比较恶劣的生存环境有关,是一个值得探究的人类文化学命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锦屏、黎平一带“偢家”村寨均实行“近拒远交”的婚姻制度,只与“偢里”中的锦屏县美蒙、岑梧、九佑、中仰、高表和黎平县乌勒、乌山、岑堆、卑嗟等“偢家”通婚。因各“偢家”村寨间相距多为数十里,年轻后生找姑娘玩山均得包饭,到姑娘村寨后,男女青年互相以歌传情,往往一次集体交往即七八天,后生受到女方合寨的热情款待。以前,“偢家”生活的村寨,生计都比较困难,所以“偢家”婚俗中,聘礼必须有六斤盐。因路途遥远,山高林密,常有虎豹出没,新娘出嫁得有男子持刀枪护送。美蒙张姓人家农历十一月“过冬节”,祭祖时再现祖先迁徙时的情景,即得备有糍粑、腌鱼、干菜等作祭品,祭桌旁还得挂有箩筐、扁担等挑具,祭者得默念祖先迁徙的艰辛历程。 美蒙村后的唱歌坪是青山界四十八寨古歌场,一年一度的青山界“四十八苗寨土王歌会”是锦屏、剑河、黎平三县青年男女的相聚之日,百里苗乡的人们穿上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到青山界唱歌坪和白岩塘天池边,赛芦笙、对歌、斗牛、斗鸟,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作为距离歌场最近的村寨,天性喜欢唱歌的美蒙人,心里掩藏着一个秘密:近二十年来,青山界歌场迎来了复兴之势,看到邻近的几个村寨分别轮值在古歌场上承办了一届又一届歌会,美蒙人也坐不住了,正在谋划着,明年的春节,在村里办一次民族歌会,邀请周边村寨的乡亲来唱歌、斗牛娱乐。 当晚的“院坝会”上,我们感受到了“偢家”歌谣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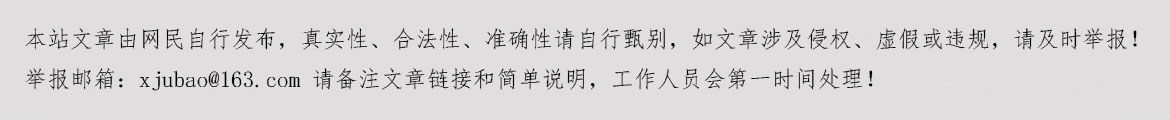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