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供应 无烟煤滤料 无烟煤滤料厂家 过滤水用 聚亿净水
北京皮村,在2017年4月,备受媒体关注。 这里出了个“打工文学作家”—— 范雨素。 她一生的好运,都留给了文学。
她一篇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火爆全网。 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在微信端迅速突破10w+,取得400万阅读量。 网友称其写作风格是“无声之处有惊雷之声”。 更对她“育儿嫂”和“作家”分裂身份感到好奇。 文章发布两个小时后,就有出版社联系她,邀请她出书。 50多家自媒体和出版社,寻着味冲进皮村,找这个“育儿嫂”作家。
范雨素一夜成名。 但之于范雨素,她不过是误打误撞。 “我之前连非虚构文学这5个字都没听过。” 范雨素说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心里堵得慌。 她和母亲打电话,听对方抱怨生活的苦。 她觉得愧疚,要是自己有钱,老人也能享受好日子。 想到这里,她铺开稿纸,把感受和经历写下来。 她甚至不确定,这篇文章能不能被选用。 但自己被治愈了,内心的阴郁都散了。 没想到,专家却给了意外的高评价。 他们觉得范雨素的文风有种“无为之技”,直接干脆,不矫情。 评论员曹林这样点评: “她的自我表达, 打破了主流社会对底层视角的垄断, 打破了固化的阶层叙述所形成的盲区,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自以为熟悉却很陌生的生存世界。” 有评论家甚至说,每个中国人都能从她文章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种评价太夸张,但直接将范雨素捧上天。 她瞬间成为了流量本身。
然而,这种成名却让范雨素十分困惑。 她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漩涡。 她去哪里,媒体就在哪里。 先是把范雨素堵在皮村文学社办公室里,请她讲讲自己的写作初衷和过程。 一折腾,就是整整10个小时。 随之而来,是各大出版社、平台的软磨硬泡。 理想国出版社希望与她签约。 某个出版商直接拎着20万现金,出现在她家门口。 网站育儿频道来请范雨素去做编辑。 有平台说要签约她,给她开公众号,一个月只要写4篇文章足矣。 报酬是1w/月。 狂轰乱炸的短信让手机死机。 那段时间,总有人在范雨素家外面观望,鬼鬼祟祟。 逼得她只敢躲在房间里,天黑了才出门。 皮村文学社办公室门口,停满了汽车。 媒体们就像一波波蝗虫,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范雨素远在襄阳的母亲,也逃不过媒体围堵。 耄耋老人被一堆话筒、摄像头围在中间,又恐惧,又不适。 房东也埋怨范雨素,那些来找她的媒体,严重干扰到周围人的生活。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超过三十家媒体来到皮村,要采访范雨素。 那天,皮村社区工友文艺联欢会恰好举办。
他们便在晚会之前增开了一个新环节“范雨素报道媒体说明会。” 有媒体记者问,“范雨素会出席吗?” “可能参加。” 很快,皮村文学社的成员小付出来否定了。 他说范雨素最近都不打算面对公众。 她害怕了。 “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
她发了一条微信,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手机关机,静静读完一本书。 范雨素真的不在意媒体的关注吗? 她是在意的。 私底下她密切留意网络上对她的评价。 有一篇文章说她是因为中产阶级的悲悯而出名。 为此,她有点难过。 “我只是真实,平视了我们的生活。” 此后,她就有些抵抗类似的讨论。 有相关宣传单位来邀请范雨素上节目,她拒绝了。 “我可不要当一盘菜,让人吃。” 她看过很多底层出名的人,上节目就是配合主办方。 点头哈腰,阿谀奉承。 一会儿感谢这,感谢那。 一会儿又要回答些无聊问题。 她不喜欢。 范雨素知道,一篇文章根本不可能改她的命。 北京的3、4、5月,是沙尘暴的频发季。 此时的范雨素,就像是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 天空灰蒙蒙一片。 容易糊眼,看不清路。
很多人觉得,范雨素早就脱离了底层。 毕竟,她出名了。 大大小小都算个红人,能出书,也能去给人演讲。 再不行,投稿写文章总比做保洁赚钱吧。 可实际上,范雨素仍旧是那个范雨素。 她依旧住在8平米的小房间。 邻里之间,没有串门,只是见面打声招呼,仅此而已。 “很多人说我成了网红, 但对我个人生活而言, 没有任何改变。 就像哪儿着了火,大家都跑去看,看完拉倒。 新闻不就是这样吗? 我心里没一点感觉, 每天还过着萝卜白菜豆腐的生活。”
走红对她来说,根本没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 每天六七点起床,赶公交到市区,去给别人做保洁。 有活就多做一些,没活就少做一些,多点时间看书、写作。 范雨素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话: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 我们活着,我们挣扎,我们照常活着。” 有人夸她清醒,乐于清贫。 但她更像是被困在理想与生存的夹缝里,拼命扑腾。 她虽然抵触媒体,但不可否认,一夜成名对她来说是个机会。 范雨素心中的文学梦,迎来一丝曙光。 她看中理想国出版社的诚意,签了约。 理想国希望她能继续写非虚构,这也是中产阶层喜闻乐见的作品。 但范雨素不想再拿自己的苦难史做文章。 双方没能达成合作。 几经波折,她终于找到“如意郎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下了范雨素。 她辞去了育儿嫂的工作。 每天在8平方的小房间里,埋头创作。
但合同规定要出书后才有钱。 日子一天比一天拮据。 “干体力活才能有饭吃,写东西能赚什么钱。” 大女儿从上海打电话给她,冷冰冰的指责。 “你啥名人,人家鹿晗、王俊凯才叫名人,你看你穷成啥样,好意思叫名人。” 小女儿也跟着嘲讽。 文章出名后,外界所有人都在等着范雨素再给大家带来惊喜。 可范家上下,却统一阵线。 “名气不能当饭吃,当好月嫂带大娃子。” 范雨素的妈妈“规劝”女儿,农民家孩子就别折腾。 “不实际,写文章难道还能当饭吃吗?” 大女儿甚至删掉了范雨素的微信。 她和记者说,母亲写作成名后,她就再也不看文学了。 “看文学小说, 很容易沉浸在故事里, 会让每个穷困潦倒的看书人觉得, 自己也能成为写出这种书的人。 很多人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的区别。 想以写小说为生的人, 他们的生活可能因为这个梦想放弃所有, 变得支离破碎。 看历史书, 人们只会看到那个成功的人, 看不到破碎的大多数人。 如果他们换个方向,生活会过得很好。” 大女儿这段话,耐人寻味。 对于母亲的走红,女儿们很是不屑。 “网红是靠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经历来涨粉,作家是创作作品,不一样。” 之于家人而言,范雨素可能算得上网红,但绝对不是个作家! 她写作,就是一场空虚一场梦。
范雨素的前半生,靠着文学熬过穷困潦倒,也借着文学一鸣惊人。 但写作成名并没有给她的人生带来任何转机。 她的前路仍像北京的雾霾天,迷雾重重。
成名过后的范雨素,也发表过几次散文随笔。 但反响平平,无人问津。 她就像落入海洋里的一块顽石,溅起一点水花便沉底。 2019年,《人物》栏目举办了一次女性主题演讲,邀请了范雨素。 她自嘲道: “我是一个过气的网红, 因为过气了, 从去年记者找着采访的车如流水马如龙, 到今年, 门前冷落车马稀, 天上人前, 物是人非又一年了。”
褪去身上“网红”的光环,她还是那个家政工。 每个月拿着2/3000元工资。 1000元给读高中的小女儿做生活费。 700元交房租,剩下的自用。 她说平日一个馒头就能顶一整天。 或者吃个6块钱的盒饭。 有记者问范雨素,你是不会用电脑,所以才用手写文章吗? 她回答,“我会打字,拼音打字很熟练,但买不起电脑。” 从她参加皮村文学社开始,她在写作上已经用了15公斤的纸,2000支笔芯。 从专职育儿嫂转成小时家政工,她的日子更清苦了。 记者问她,“为什么没想过“收割”自己的流量?” 范雨素说:“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我不想当网红,在人堆里生活,我不付出,也得不到。” 记者又问:“为什么没把写作当成职业?” 她说,“靠写作这条路,要写得好、有读者才能过好。 你要写得不好,没读者,都还不如做体力活赚钱多。 我没有那份自信。 我没有希望靠着文学能得到什么, 连这些名声我都觉得是‘天降横财’。”
范雨素曾经有个很大的梦想。 她想要成为中国的“第欧根尼”。 第欧根尼是哲学家,每天睡在垃圾桶,不慕荣华富贵。 但亚历山大大帝等人都很尊敬他。 再谈及这个梦想,范雨素只是笑笑,很是不屑。 “小时候懒,总想着不用干活。 如果真做第欧根尼的话, 我已饿死了好几回。” 她眼里不再有光。 文学对她来说,不再是理想,只是港湾,一个休闲的地方。 她也不再是那个逃跑的孩子。自命不凡,心比天高。她认了命,知道在庞大的、坚硬的现实面前,人力真的太微弱。 为了生计,她弯下腰,继续找生活。 范雨素的身上,是无数底层人民的缩影。 他们在生存与理想中挣扎。 理想只能是浅尝辄止,一枕黄粱,最终都要醒来。 “我的梦想也不会拖很长时间啊, 我不可能说一生都追求文学吧, 最多几个月或者一年, 我就把这件事结束, 老老实实做人。”
记者问她,“什么叫老老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就是去找一份体力活,做育儿嫂或者别的,老老实实做事情。” 她说这话时,思绪回到了90年代初。 她初来北京时,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要赚多点钱,在北京买个房。 作者:阳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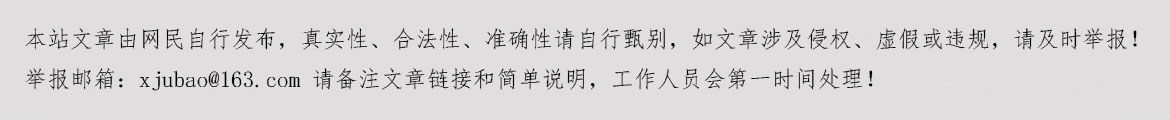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