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入过万的小生意 https://www.touzitop.com/ysjx/5836.html
2009年夏天,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那甘纳吉村,我们见到了40岁的寡妇珊塔玛,她是6个孩子的母亲。珊塔玛的丈夫4年前死于急性阑尾炎,她没有保险,家里也拿不到任何抚恤金。三个年长一点儿的孩子都上了学,至少上到了八年级,但另外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一个10岁男孩和一个14岁女孩)都辍学了,女孩在邻居家地里干活儿。我们认为,由于父亲的去世,孩子们被迫辍学,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便开始干活儿挣钱。 然而,珊塔玛纠正了我们的想法。丈夫去世后,她便将家里的地租了出去,自己开始干临时工,挣的钱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需求。 珊塔玛的确让女儿去田里干活儿,但那是在她辍学之后,因为珊塔玛不想让她待在家里没事儿干。其余的孩子都在学校上学——在三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中,有两个在我们见面时还是学生(最大的女儿22岁,已经结婚了,很快就会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 我们了解到,她的大儿子在最近的城镇雅吉尔上大学,将来准备成为一名老师。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之所以辍学,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去上学。村庄附近有几所学校,包括一所公立学校和几所私立学校。那两个孩子原本上的是公立学校,但他们经常逃学,最终母亲放弃了让他们上学的打算。在我们采访期间,那个10岁男孩一直和他的母亲在一起,嘟囔着上学没意思。 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上不起学。在大多数国家,上学是免费的,至少上小学是如此。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学可上。然而,我们在全球所开展的各种调查显示,儿童辍学率在14%~50%之间。辍学往往并不是由于家里出现了紧急情况,有时可能是健康原因所引起的,比如在肯尼亚,孩子们会因接受抗蛔虫治疗而耽误几天课。 尽管如此,辍学情况或许还能反映出,孩子们并不想上学(这可能很普遍,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这种状态),而且他们的父母似乎也无力或不愿让他们去上学。 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这也意味着,全面提升教育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如果没有强大的潜在教育需求,那么建立学校、聘用教师又有什么用呢?相反,如果人们对技术有真正的需求,那么对于教育的需求自然就会显现,供应便会随之而来。然而,这一乐观看法似乎与珊塔玛孩子的故事不相符。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是印度的IT中心班加罗尔,它对人才的需求量自然很大。珊塔玛一家中有一位未来的教师,他们意识到了教育的价值,因此愿意进行教育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学生不具有吸引力既不是因为入学难或缺乏人才需求,也不是因为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那么,阻碍究竟源自哪里呢? 供求之战 教育政策就像援助一样,一直是激烈的政策之争的主题。正如援助一样,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每个人或许都会同意,受教育总比不受教育要好),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而且,尽管教育与援助所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但二者内部的分界线实际上处于同一位置,提供援助的乐观主义者们一般都是教育干涉主义者,而提供援助的悲观主义者们一般都支持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 长久以来,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至少是国际政策领域)一直认为,教育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先将孩子们带进教室,最好由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师任教,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这类人强调“供应学校教育”,我们将他们称为“供应达人”。 这里借用的是印度的一个俗语——“供应商”(西印度语中的这类绰号有拉克达瓦拉——木材供应商、达路瓦拉——酒品供应商、邦度瓦拉——枪支贩卖者等),以便与供应经济学派区分开来。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或许,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供应达人立场的最清晰的表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于2000年取得共识的8个目标,预计在2015年之前实现。其中第二、第三个目标分别是,“确保到2015年世界各地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完成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以及“到2005年,争取消除初中等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并在2015年之前消除各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在印度,目前95%的儿童可以在距家不到半英里的学校上学。3几个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加纳)已开始提供免费的初级教育,大批孩子进入学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在1999~2006年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小学入学率由54%上升至70%,在东亚及南亚则由75%上升至88%。 全球学龄儿童的辍学人数由1999年的1.03亿减少到了2006年的7300万。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即使是那些极为贫穷的人(每天生活不足99美分的人),其子女入学率目前也在80%以上(被调查国家中至少有9个国家是这样)。 虽然普及中等教育(9年级以上)并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部分,但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5~2008年之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学入学率由25%上升至34%,南非由44%上升至51%,东亚则由64%上升至74%。不过,中学的学费也变高了:聘用教师需要更多的钱,因为这些教师必须是更有资质的;而且对于父母及其子女来说,他们放弃的收入及劳动市场经验有更大价值,因为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干活儿挣钱了。 让孩子上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正是学习的起点。然而,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么上学对他们来说就毫无用处。有些奇怪的是,学习的问题并未被摆在国际声明中十分突出的位置: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没规定孩子们必须在学校里学到东西,只是说他们应完成基本的课程。 2000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全民教育峰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在峰会的会后公报中,提升教育质量的目标被排在了第六名,即第六个目标。这其中的隐含意义或许是,学到什么没有入学重要。然而,遗憾的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2002~2003年,由世界银行发起的世界缺席调查秘密派出一些调查员,到6个国家的公立学校进行抽样调查。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孟加拉、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的教师平均每5天就会缺席1天,其中印度和乌干达的教师缺席率是最高的。此外,印度的调查显示,即使教师在校并授课,他们也经常在喝茶、读报或是和同事聊天。总体来说,印度公立学校50%的教师都在上课时间缺席。5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学习呢? 布拉翰(Pratham)是印度一家专门致力于教育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于2005年决定进行深入研究,查明孩子们究竟在学些什么。布拉翰成立于1994年,其创立者为化学工程师马达夫·査万。査万拥有美国教育背景,他在创立布拉翰时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所有儿童都应该学会阅读,并通过阅读来进一步学习。 该组织成立之初,查万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下,将这家位于孟买的小小的慈善机构。发展成了印度最大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或许也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布拉翰的计划涉及约3450万印度儿童,而且目前正深入到世界其他地区。 在《年度国家教育报告》(ASER)的指导下,布拉翰在印度的600个地区建立了志愿者小组。这些小组在每个地区都随机选择了几个村庄,对每个村庄的1000多名儿童进行了测试——参加测试儿童总数为70万——并总结出了一份成绩单。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看到了这份报告,但他从中所读到的却令他心情沉重。7~14岁年龄组中接近35%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段落(一年级水平),而几乎60%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二年级水平)。只有30%的孩子会做二年级的数学题(基本除法)。 这些数字令人十分震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在自家的摊位或商店里帮忙,总是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作一些更复杂的计算。难道学校让孩子们变得不会学习了? 并非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像阿卢瓦利亚先生一样豁达。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就拒绝相信政府的表现如《年度国家教育报告》所暗示的那样糟糕,于是便组织自己的团队再次展开测试。很遗憾,测试结果只是印证了原有的数据。1月,在印度的一次年度活动上,ASER的测试结果被公之于众。报刊对可怜的测试分数表示沮丧,学者们在专题小组会上讨论着那些数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印度并非个案,其邻国巴基斯坦、遥远的肯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肯尼亚,效仿ASER的尤维佐调查发现,27%的5年级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英文段落,23%的孩子读不懂斯瓦西里语(小学的两种教学语言),还有30%的孩子不会做基本除法。7在巴基斯坦,80%的三年级孩子读不懂一年级的课文。 需求达人案例 一些批评家(包括威廉·埃斯特利)认为,除非有明确需求,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供教育。对于需求达人来说,这一结论涵盖了几十年来所有教育政策的缺点。在他们看来,教育质量之所以低下,原因就在于家长们对教育不够重视,他们觉得教育真正的好处(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教育回报”)并不多。
当教育回报足够高时,根本无需政府的推动,入学率自然会提高。人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专门的私立学校,如果私立学校学费太贵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当地政府建立学校。 需求的作用确实很重要。入学率与教育回报率息息相关:在印度的“绿色革命”期间,成为一名成功的农夫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学习的价值也有所上升。在一些更适合播种“绿色革命”所引进的新种子的地区,其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近期,离岸呼叫中心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欧洲及美国,人们常常指责这种呼叫中心减少了当地的工作机会,但它却大大增加了印度年轻女性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印度一次小规模社会革命的一部分。200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延森与一些这样的呼叫中心合作,随机选择了印度北部3个城邦很少有人去招聘的几个村庄,在那里组织针对年轻女性的招聘会。 结果在意料之中,较之其他一些未实施这种招聘方式的随机选择的村庄,这些村庄业务流程外包中心(BPOs)的年轻女性的就业率得到了提升。更为显著的是,这部分地区原本可能是印度歧视女性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但在招聘工作启动三年之后,招聘点所在村庄中5~11岁女孩入学的概率提高了5%。这些孩子的体重也有所增加,这表明家长们将他们照顾得很周到:他们发现,让女孩受教育同样会带来经济价值,因此乐于投资。 在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应方面,家长们有能力应对变化。因此,对于需求达人来说,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没有教育政策。只要找到一些急需人才的行业,让投资于这些行业变得富有吸引力,那么就会出现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方面的供应压力。 这样,争论便会继续下去,因为家长们开始真正关心教育,他们会向教师施压,让教师根据他们的需要授课。如果公立学校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私立学校市场便会趁势形成。有人称,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会让家长们得到适合他们孩子的高品质教学。 需求达人观点的核心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人们投资于教育,就像投资于任何其他领域一样,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的收入。将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做出投资的是家长,而未来获得收益的是他们的孩子。 而且,尽管实际上很多孩子会为他们的父母带来投资“回报”——给他们养老,但很多孩子并不愿那样做,甚至“不履行义务”,将他们的父母遗弃。即使有的孩子很孝顺,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因多上了一年学而多挣的那一点点钱,能够转化成父母们的收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心生悔恨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非常富有,可以在外面自立门户,却让他们晚景悲凉。 保罗·舒尔茨是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自己的父亲——著名经济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时说,父母曾经反对他上学,因为他们想让西奥多留在农场。 的确,孩子学习成绩好,家长也会为之自豪(他们喜欢与邻居分享这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家长从孩子那里得不到一分钱,他们或许也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因此,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仅是一种投资,而且还是他们赠送给孩子的礼物。 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家长都有权支配他们的孩子——由他们来决定谁去上学,谁留在家里或是出去工作,以及他们的收入如何支配。有些并不重视教育的家长很在意孩子长大后会回报给他们多少钱,这样的家长或许会在孩子10岁时就让他辍学,并安排他出去工作。换句话说,教育的经济回报(其衡量尺度为受教育孩子的额外收入)固然很重要,但其他很多因素或许也不容忽视,比如我们对未来寄予的希望,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以及对自己的孩子是否宽容。 “没错,”供应达人说道,“这就是有些家长需要点化的原因。儿童有权利享受正常的童年及充分的教育,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允许这一权利被父母的冲动或贪婪所剥夺。”要降低送孩子上学的费用,建立学校、聘用教师是必要的一步,但这或许还远远不够。 这一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富裕国家都强制规定:当孩子达到一定年龄时必须送他们上学,除非父母能证明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教育孩子。然而,这在国力较为有限、义务教育难以强化的情况下,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从经济角度考虑,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是值得的。这就是教育政策所选择的新工具背后所折射出的理念:有条件现金转移。 【本文节选自《贫穷的本质》,作者:阿比吉特,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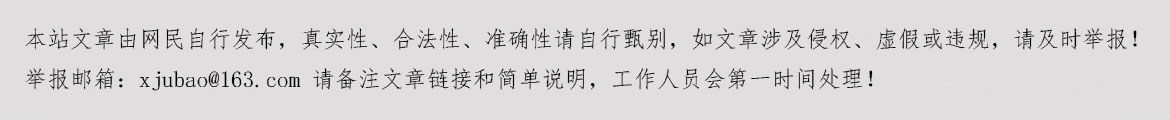
|